作者:杨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
16至18世纪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部分。但从总体上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海内外均偏重于西学东渐一脉,其主流并不体现为中西文化双向互动的多层次探索。相比西学东渐领域已取得的成果,中国学者仍然缺乏针对中学西传的系统研究。
为了打破此种单向度趋势,张西平教授二十余载孜孜不倦,以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为首要前提,致力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全方位研究海外汉学。他遍访欧洲、追踪整理失落的欧藏中国文献,逐步建构起儒学西传欧洲研究的学术大厦,为人类文明史找回中学西传这只“遗失的翅膀”。其新作《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更集合了作者长期坚持的学术导向与最新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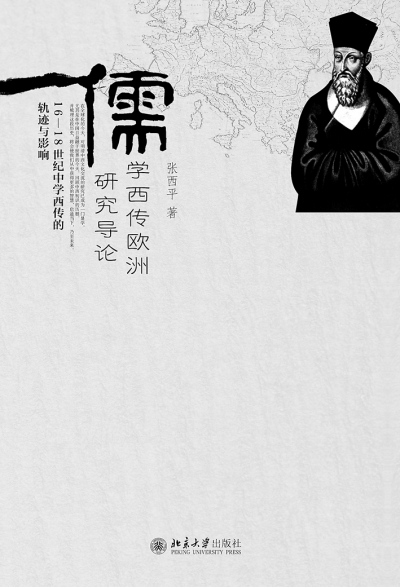
找回遗失的翅膀——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
《导论》首先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晚清以降,在有关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话语表述中,极少将中国和西方放在同一架天平上,给予足够的、被平等审视的机会。检视20世纪有关近代中西关系的西方汉学著作时,我们能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论述,隐藏着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的情感预设。从西方中心主义、基督教中心主义出发,对中西交流进行评价和考量,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前提,导致海外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关注西方文明怎样参与对近现代中国的改造,而不是中国文化如何像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照亮我们这个时代”。张西平教授以相当的魄力和勇气,打破学术传统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重新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他在《导论》中批评了中西文化交流史单向化、片面化的研究现状,提出应该把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西译,传教士的‘西学汉籍’和中国历史的西语文献报告和著作的研究,是改写目前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对于它们的细致研究,将是解开全球化秘密的关键所在。唯有此,历史的真相才会呈现出来。”难能可贵的是,它并非一味抨击西学东渐的相关研究,以此塑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学术言论,而是以公正开放的态度,首先肯定西学东渐研究的学术价值和重大意义,表示相关研究仍然需要继续加强。但对西学东渐的推崇,不应掩盖甚至有意识忽略中学西传的历史事实与重要作用。缺乏对中学西传的研究,整个中西交流史的学术大厦会失去平衡。只有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比翼齐飞,才能使我们在兼具全球眼光与中国情怀的批评与对话的前提下,正确理解汉学研究的实质。
其次,《导论》对西方文化自我成圣观提出了批评。本书为我们讲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力被解构和祛魅以后的故事,一段关于16至18世纪中西文明之间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平等交流与自主融合的历史。它从传播史的视角出发,着力重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文化通过怎样的路径流传到西方,又对西方世界产生过何种影响,展现中国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证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产生于单一的欧洲思想内部”,而是通过从其他古老文明里获得启示,形成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的线性历史观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调的历史观念,即西方文明的演变进步并不是地域性的单向因果递进关系,而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通过学习、吸纳及改造其他文化的资源,创造了所谓“西方的胜利”。
与此同时,该论著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费孝通先生提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导论》对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它凭借翔实的史料,通过法国重农学派与孔子学说之关联、莱布尼茨对宋明理学的学习、伏尔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等例子,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拔擢至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之深刻渊源这一思想层面。在中学西传的进程中,中国文化尽管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但因其具有的人类共同价值与进步因素,为启蒙运动所借鉴吸收,“借助中国和孔子,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该论著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国族主义的限制,解构了“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在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时,我们不能将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相反,我们可以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理解中,纠正偏误,赋予儒家文化以符合现代生活的新意,开出启蒙思想之新意。”通过真正挖掘、理解启蒙运动的发生、衍变,重现中国文化如何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从学理上作出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多元复杂关系的综合性分析解释。当被忽视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曾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启蒙思想的事实浮出历史地表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思想内涵,经过改造也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资源”。
从学术贡献的向度上进行衡量,《导论》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突破。第一,重新定义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的历史地位。关于中学西传的滥觞,绝大部分学者,如方豪、朱维铮、汉学家夏伯嘉等,将这份殊荣授予利玛窦。张教授则对该经典论断发起了挑战,通过翔实的史料比对及手稿分析,拂去历史的尘埃,考察发掘了罗明坚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之第一人的事实真相,肯定他为中学西传乃至西方汉学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对中学西传源流所作出的专门研究,更是世界范围内率先开展的,有关罗明坚儒家典籍翻译的研究。该成果的披露,对西方学界占据语言、地域与资源优势,垄断中译西、中文文献西传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是一个极大冲击,证明中国学者在西文文献和手稿材料的跨语际研究实践中,克服了语言交流障碍、史料搜集整理等困难,也开始崭露头角,公平竞争话语权。
第二,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实质性突破。《导论》开拓性地从中国典籍翻译的角度展开中学西传研究,详细阐述罗明坚等传教士个体和来华耶稣会等机构如何承担起中国古代经典西传桥梁的作用。作为第一次全时间描述16至18世纪中学西传总体面貌的专著,从传播史的视域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做出实质性突破。
在现代西方学界,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出现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等一系列论著。尽管我们承认这些专著的出现,代表着海外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文明自我成圣观,肯定东方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但实际上,很多著作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展开研究,而是将东方视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把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合而为一,纳入所谓的东方文明范畴中。因此虽然讨论的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研究者却很难彻底摆脱以“他者”身份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主观想象。与之相反,《导论》是一部植根在中国而非西方话语经验中的史学论著,作者开创性地从一个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和学术视角出发,满怀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打破了西方汉学界建构于自身价值体系审视中国文化的“单相思”。
第三,是对翻译学的探索和推进。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典籍外译的研究大部分套用西方已有的翻译理论来解释“中译外”问题。特别是关于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翻译的讨论,体现出紧跟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倾向。《导论》则立足本土,保持研究中理论和文化的自觉性,对风行于当代翻译研究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持谨慎态度。“基于语言和哲学思维的不同所形成的‘中译西’和‘西译中’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践,我们应该重视对‘中译外’理论的总结,现在流行的用‘西西互译’的翻译理论来解释‘中西互译’是有问题的,来解释‘中译外’更是一个问题。”在详细考量以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译外之不合理性后,张西平教授坚持学术自主,独立总结更为合理可行的翻译理论,用以分析西译汉籍。在解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具体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构建出“联系与变动的混合关系”模型。在该理论系统内,所有翻译,都可以被视作“保留与改造”的混合产物。也就是说,“在研究任何文化间的翻译时,仅仅强调‘变动’而忽略了联系,就无法理解文化之间过渡的可能性;同样,在翻译研究中如果只强调译者对原文的‘改造’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看不到这种‘改造’和‘保留’的内在联系,则会将原文和译者之间脆弱的关系完全割断”。由罗明坚等传教士开启的“中译外”历史充分说明,翻译中纯粹的“信”只是一种理想化效果,但将翻译完全理解为译者的个人创造,又走向了另一重极端。“译者和文本之间是‘联系与变动的混合关系’,其翻译作品是‘保留与改造’,翻译的历史就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
第四,是引领了中西交流研究的新方向,在研究方法论上做出了带有批判的继承与创新。针对史学研究中多语种资料的运用,张西平教授一直呼吁关注欧藏中国文献的重要作用,重视西文材料和中文文献的对比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大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展现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以比较文化和全球化的视角,用更广博的心态看中西交流。且张教授阐发议论的同时,在书目尾声不忘作出一个初步的研究总结,探究16至18世纪中学西传研究滞后的原因。将自己多年研究所得的宝贵经验和发掘出的学界空白倾囊相授,为继起者指出了未来研究中切实可行、有待发扬光大的新领域。
随着21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再一次展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审视与评估。《导论》从传播学、跨文化、新史学等角度,结合中西材料,再现16至18世纪儒学西传历史过程中关键的人物与事件,对中学西传这一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展开系统性研究。总结过去的同时把握将来,在史料、论点和方法上均取得新建树,弥补了一系列学术空白。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拾现代价值、走向世界的今天,这本著作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中西交流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重建中华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