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在黄河出海的山东大地上,有一个人的思想,对后代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孔子。
话说当年,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年代,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当此之时,有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怀着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挺身而出,来为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治国之道”。于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大幕,便开始从中原大地转向了泰山脚下的山东半岛。
在这片“齐鲁大地”之上,先有儒家的孔子出来主张“无讼”、倡言“复礼”,继而,又有墨家的墨子起来力言“非攻”(反对战争)、“法天”、“法仪”(即提倡自然正义),接着,更有孟子高扬“民本”、“民权”,发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呐喊。这边厢,当道家的老子、庄子在嬉笑怒骂、辛辣讽刺一切统治阶级的“实在法”时,那边厢,儒家的荀子却又在大声呼唤着“圣人之治”。在荀子主持的“稷下学宫”里,却忽然后院起火,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一大批自由派思想家们,在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学说基础上,广纳百家学说的理论精华,又发展出了风靡一时的“黄老学派”,力言执政者要“抱道执度”、“约法恤行”。
平心而论,在这个时期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真的是一个空前绝后、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有一个很少为人所注意的历史细节是:早在老子骑牛出关,并挥笔写成《道德经》这部伟大的著作之前,在黄河对岸的中条山下,魏国的李悝亦已悄悄编成了一部著名的《法经》。但这部《法经》很不幸,抛弃了自周公以来所有古代法学家们曾经有过的对“法律的本质价值”的种种思考,而重走了商代那条“以刑代法”、“以刑治国”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旧路,并由此而在中原大地上,开启了一个“专任刑杀”、被称为“法家”的学派。其后不久,在河南、陕西等地,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一个接一个著书立说,大力鼓吹“君主专制”、“严刑峻法”,于是,中国法律史的风向,又再从山东半岛,转回了中原和陕西大地。
综观这一场长达二三百年的中国法学的“百家争鸣”,有一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那就是:“墨”、“道”两家的法学智慧,由于十分不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之中,长期被打入冷宫、遭人忘却。而“专任刑杀”的法家,虽然曾一度大受统治阶级的青睐,但在经历过一番短暂的疯狂之后,很快跌落到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境地。只有孔子的儒家学说,虽在秦始皇时代亦曾经饱受“焚书坑儒”的迫害,但在西汉初期,却又终能卷土重来,不仅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之所“独尊”,更成为“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而且还能在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被历代帝王们尊奉为中国官方法律思想的正统。
这里面到底又有什么缘故呢?
原来,“圣时门”这三字,源出于孟子文章中的“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其意是赞扬孔子能“审时度势”、“适时应变”地处世为人。不过,在孟子这句话里,也分明含着另一种意思,即——无论时势怎样变化,从孔子的思想学说里,总可以找到一些能为统治者所用的东西,所以,孔子才能两千年不倒地“时尚”下去。那么,在孔子思想里这些很“行时”的东西又是什么呢?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做过一段很精辟的分析:第一是孔子的“天命”观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可以用来对人民实施“愚民政策”;第二是孔子的“大一统”观念——“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可以用来理直气壮地镇压所有乱臣贼子;第三就是孔子的“纲常教义”——即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归纳为“三纲五常”,并通过对君权、父权、夫权这“三纲”的确立来统领“五常”——“仁、义、礼、智、信”,巧妙地把“事亲之孝”,转化为“事君之忠”,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一种伦理政治体系,并将“防止犯上作乱”、确保人人都是“天子顺民”的政治责任,“关口前移”到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里,让每一位族长家长去承担。
因此,不难明白,自西汉以来,孔子这种大有益于帝王的“人治”、“德治”,而总不提小民们的“权利”与“自由”的学说思想,为何会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并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立法思想的圭臬。
不过,在近代百年众多学者(包括王亚南先生)对孔子“纲常教义”的猛烈批判之中,我也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意见。考诸《论语·颜渊》的原文,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是说,“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从中我们并不能推论出孔子提倡“君权至上”、“父权至上”的牵强结论。而同时,从遍布整部《论语》的那些“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孔子言论中,亦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味地要求下级对上级盲目顺从,而是对上下级双方都提出了一种对等的、合乎人性的,甚至可以说还包含一种相当现代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法律精神在内的道德要求。
作为一个思想家,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孔子完全有权自由地发表他个人的思想见解,而我们却无权在现代“自由地”歪曲他的原意。至于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谬论,只是西汉那位董仲舒歪曲了孔子的原意而自编出来的。而至近代,许多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一腔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对“吃人礼教”的所有板子,都毫不留情地打在孔子身上,这种情况,对孔子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遥想当年,孔门的三千弟子曾在此地云集听经,而孔子则正襟危坐、高台教化,洙水河畔,弦歌声声,这种空前的文化盛况,令我产生一种对孔子人格的感动。
现在,我已来到了孔庙的最后一重宫殿——“大成殿”前。
说起来,这“大成”二字,亦源出于孟子的章句。其本意,也只是赞扬孔子是位继承了众多古圣美德的“集大成者”,而并非是说孔子的学识文章已“集天下之大成”。流连在这座孔庙中最巍峨壮丽的大殿之下,手抚着那些雕刻精美的蟠龙石柱,遥望着烟雨空蒙的殿外,只见有不少的游客在雨中焚香礼拜,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他们究竟是在祈祷些什么。而转头细观殿内,则见一尊被神龛上面的帷布遮住了半个脑袋的孔子塑像,高高在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些万万千千、熙熙攘攘的游客,在自己的面前日夜来去。
看着这位寂寞的孔子,我忽然生出了一种啼笑皆非之感。
可悲的是,2500年来,这个被摆上了神台的人,其思想言论,却又长久地遭到人们普遍的误会和曲解——要么被人肉麻地吹捧,要么被人刻薄地批判。
说起来,在孔子毕生的思想言论中,最能反映出他的糊涂的,就是他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一直都以为:只有“周礼”,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而中国只要复归到“周礼”的轨道上去,就一定会天下太平。但他老人家可能从来都未想过:他那种总想拿西周的“礼治”来解决春秋时期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总想教育春秋时期的人民和社会退回西周时代中的天真想法,也许真应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叫“刻舟求剑”。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晚年一车两马、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地游说诸侯而总是理想不售,徒使自己的一生蒙上了一种浓厚的唐·吉诃德式悲剧色彩的最根本原因。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终生笃学慎行、对民众进行持续不倦的道德教育的大师,孔子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史上,真的是功不可没,亦堪为“万世师表”。但从学理上来说,伦理道德,只是一种涵养自己的思想品质、提升和净化个人灵魂的修心养性之学。而法律法规,则是一种调节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增进社会的秩序与促进人群的文明的社会科学。前者适用于修炼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后者则适用于治理个人之外的外部社会,对于“治国”来说,这二者都各有其妙用,都不可偏废,亦切不可错位。但终其一生,孔子却恐怕都没有弄明白这二者的性质功能区别,而他的一生之中,亦都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一种天真信念:“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翻译成白话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要“君子们”作出了道德的榜样,“小人们”就必然会受到感染教化,就一定会像草顺从风一样地跟从君子,而那时候,人人都是君子,天下就自然太平了。
平心而论,孔夫子一生的道德文章自有其伟大而崇高的一面,但无可否认,其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之处可能也就在这里——他是否忽视了“周公的礼治思想是一种‘德治’与‘法治’的混合体”这一点,极端地推崇了“德治”这一端,而贬低了“法治”这一端?例如,他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等等,这就不仅仅是在轻视和鄙视法律,而且,简直是把法律视为一件不道德的事,进而不承认法律、否认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了。
对于孔子这种极端的“无讼主义”,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先生便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议论:“将争讼的本身当作不道德的勾当,那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有纠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社会要有一套公平的法则,有一个主持公道的地方来解决矛盾、重建和谐,而不是由官府来强行压制或“和稀泥”。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争讼”被认为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是一种“刁民”才会去干的事,因此,每当遇到矛盾纠纷,民众心里虽然有委屈,但在孔子道德说教的压抑之下,也不敢说出来,而无处申冤、无处寻求公道的后果便是:人们在忍无可忍之际,便会演变成一场互相之间的谩骂和斗殴,或者养成一种口是心非、“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伪君子性格,或私下寻求行凶报复。
这样,这个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便一定会时时充满了暴力,又时时充满了欺诈。由此可见,“社会的真正和平,人类的真正文明,都只能通过一种‘诉讼的艺术’和‘法律的科学’而磨练出来”,而“法学的昌盛,法治精神的发达,都是以争讼为基础的”(参阅吴经熊:《中国旧法制的哲学基础》)。这些议论,我意认为,真是一段对孔子“无讼”思想最婉转而又最深刻的批评。
作者简介:
余定宇,广州人,1982年毕业于广州师院历史系。曾任职新闻记者、《广州商报》执行总编。现为独立撰稿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公民教育,著有创新型普法著作《中国人,你有权保持沉默?》和《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分别为人民法院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出版,两部书打破了枯燥无味的学院派教科书式的旧框框,在中国普法文坛开出一股新风气。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界泰斗陈光中教授称作者为“在法学激流中,为中国改革出力的纤夫”。
余定宇先生2010年新作,《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已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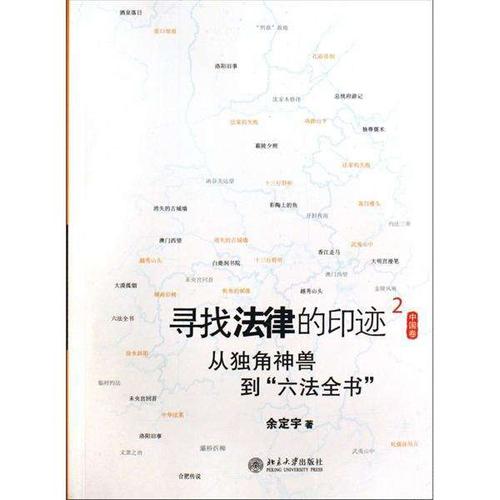
责任编辑:马晓